
_
32岁的杂货铺老板,患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。在彻底恶化前,他用一次次的流浪与自我放逐,对抗命运的虚无。在蛮荒之地,他找到另一种生活的可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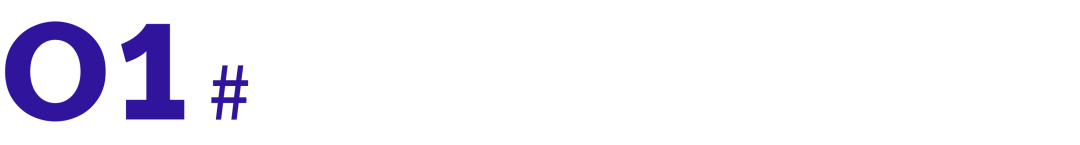
我已经三十二岁了,准备到山里建个四合院隐居酿酒。
我太爱喝酒了,喝醉了醒着不是醒着,梦也不是梦,悬浮在一个高于现实又低于梦的维度里。可现实总跟理想过不去。疫情虽然没有带走我的命,但是带走我不少钱。
九月份,我终于把经营多年的两个杂货铺转让了,滋味很复杂,即是解脱又是失落。
我和箱子们一起拥堵在三姐家的小屋里,撑得小屋要吐。属于我的只有眼前这些箱子,里面具体装的啥我也忘了,反正都有用,不过没有也没关系。
我用屁股使劲挤了挤床上堆满的杂物,呆坐在床边看着箱子们,抽根烟吧。想想这些年旅游和玩的花销在这小城换个两室一厅是够的,再想想今后何去何从?总不能无所事事吧?再抽根烟吧。
马向平的电话结束了我的多愁善感。他是北京的藏文化学者,也是苯教弟子。他要去阿里寻找古象雄遗址和壁画,也知道羌塘能让我魂牵梦绕,问我去不去?我让他等我考虑考虑。
“弟呀。姐都快急死了,你还得几天能把楼上货架给姐装上啊,货都到家了。再不摆出来就过季了。”三姐愁眉苦脸地站在门口说。
这活儿我已经磨蹭两天了,按照现在的速度起码还要一周。我很不情愿地拿起手中的小锤儿,有点沉,比划两下又放下了,总觉得平板手机上有点什么得看看,屁股一下就被椅子吸过去了。
马向平发来了这次长途旅行的文案,看着那些诱人的西藏地名我不知不觉地笑了。摸摸良心问问自己想不想去?相当想!盘算着买房盖房钱不够,跟他走,够!
小锤儿再次上手分量就不一样了,它又轻又敏捷。小锯儿锯一下木板心里就念叨一遍:羌塘!阿里!
两天一夜几乎没睡,干完啦。
出发前我妈有点担心。以前催婚,我说再催我就出家当和尚,她说我神经病。前段时间,我说想独居山里,潜心酿酒,她建议我去山里出家,起码寺庙人多安全,我没干。
“妈。我要走了你不说点啥么?“
“嗨!你现在走我都不在乎了。”她忽然想到什么,接着说:“妈跟你说让你去当和尚是跟你闹着玩呢,你去了可别真留那不回来。”
“我神经病啊,我才不出家呢。”
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
同行四人一车,北京出发。另外两个我都不认识,一个搞摄影的姚旭东,还有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天津朱玉海。
进藏后,我们先去马向平皈依的寺庙,他把这当成第二个家,想在这里多住几天。我跟他来过一次,被这里的气质深深打动。

图 | 水鸟
到了海拔四千多的寺庙,我高反了,头很疼,眼睁睁地看着玉海像野牦牛一样各各山头撒欢,还让我看它在山头光膀子的照片,他的胸毛茂密的像黑胸罩,让我更加断定它就是没进化好的野牦牛,不然哪来这么强的身体素质?
画满壁画的屋里,六人有三个时不时吸一会儿氧气,走路都吃力何况爬山。晚上玉海又说外面的星星超好看,我让他离我远点,以免我的脑袋爆炸崩着他。
很冷。我是穿着羽绒衣裤进羽绒睡袋的,高反入睡是个技术活,加上另外五个老爷们打呼噜磨牙放屁和高反的呻吟声,我放弃强求不来的睡眠,只想撑住,撑着撑着就昏了过去。
好在第二天头就不痛了,看到的天也蓝了,云也白了,诵经声也神圣了,还在风里闻到了酥油灯的藏味儿,甚至挑起了给十几个内地弟子做饭的要务。接过这个要务后我就为难了,调料只有油和盐。硬着头皮干吧,他们说熟了就行。
“师兄。这个米最多只能洗一遍,菜也是,好像之前老姜都不洗的,这里的水实在太珍贵了。大部分是从山下背上来的。”瑶瑶心疼地看我把第二遍洗米水倒掉说。
瑶瑶是一名上海医生,牙白眼亮温柔善良,在美国留学期间接触过很多种宗教,最终皈依在本寺师傅门下。她每年都会攒假到这里修行一段时间。
缺水是大问题,外来的弟子都很自觉地尽量不用水,脸也不用洗,没人笑话,这里人都这样。可我必须用湿巾擦擦脚,我很惭愧。
“兄弟。要不你还是洗洗吧,我头太疼了。”我对床的于大哥说。
之后几天,我是唯一够资格泡脚的。有人看我泡得舒服也想泡,被拒绝,他不够臭。
评论责编::admin
广告
相关推荐
热点推荐»
- 12020-01-09西藏军区司令员调离后,这位亲赴战场的新晋中将座次不一般(最新发布)
- 22018-03-102018年西藏中级会计师考试报名时间为2018年3月10日至31日
- 32018-03-022018西藏中级会计师考务报名时间通知(最新发布)
编辑推荐
- 模拟试题

